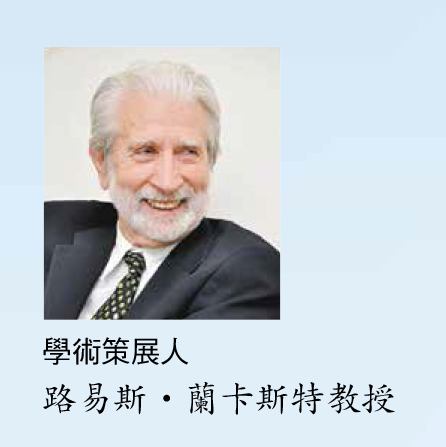
原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文系終身榮譽教授 路易斯‧蘭卡斯特 中譯/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想要製作文化史數位地圖的這個想法,在電腦和軟體科技成熟以前就已經開始醞釀了。1980年末我在大學講授「東亞佛教的歷史和發展」學士課程已有二十年,認為是時候為這主題寫一本書。當我著手於佛教從印度傳播到中國,再傳到日本、韓國、西藏和蒙古的大綱,便發現龐大的內容難以僅用一本書就可以敘述所有,這幾乎不太可能。首先,這樣的一個發想需要利用數個地圖從視覺上去展示佛教文化特徵和各種傳統及儀式的傳播性質。因此,我靈機一動,想說透過電子地圖將讀者連結到各個靜態版地圖瀏覽,是可行的方法之一。有了這個想法,我便在柏克萊發起會議,與學者、圖書管理員、博物館工作者、藝術史學家、藝術家等人,針對相關資料數據的蒐集、呈現手法以及開放予大眾等課題進行初步討論。第一次的會議共有十六人與會,在那次會議裡,我們認為我們有必要召開另一個會議,並且必須廣泛招攬具有技術背景和學術專長的人員共同參與。因此,隨後在舊金山大學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一共有七十人參加。經過那次會議整整兩天的發表、討論和演示,我們不得不面對這麼一個事實:會議或研討會不是只舉辦一次,就足以解決所有涉及其中的複雜性和難題,這如同無法在一本書裡就能將佛教傳播的所有細節完整講述。了解到我們還需要舉辦很多次的會議、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和技術專員來處理眼前的複雜問題,一個新的組織「電子文化地圖」(ECAI)因此而創立。我很榮幸地,擔任ECAI的主席一職,迄今已有二十餘年,並在歐洲、亞洲、澳洲和北美等地,舉行過將近百次的會議。ECAI的組織定位,從來不是要完成一個什麼最終成品,而是鼓勵學者多元思考當前的議題,並在聆聽與自己的領域相差甚遠的各項工作時,聯想到自己的專長和技能可以如何協助並分享予他人。
在ECAI召開會議發起進行的各項工作當中,其中最重要的發展項目是繪測技術和其在學術界扮演的角色。經過在舊金山召開的第二次會議,我們就已經清楚知道,再多的靜態地圖,都不是最佳表現文化在特定地點之傳播動向和影響的方式。在人文領域的我們不得不考慮採用新科技,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統(GIS)這個軟體。多年以來,GIS只侷限於軍事用途,因為它可以檢測到某個地標的精確位置。雖然它單純是個由經度和緯度組成的座標系統,但透過電腦劃分,經緯度的細線可以小至只有幾米的範圍,並定位在地球上的任何一處。很幸運的是,隨著其他國家逐漸開發出各種形式的GIS,這個軟體不再被視為機密技術,政府也漸漸開放予公眾使用。初期的開放是有侷限性的,以避免公眾濫用精準的地理定位作為妨害公共安全的武器。儘管軟體功能的侷限性,但這開放給大眾使用的早期版本,也為人文領域提供了一個新的工具選項。
這跟任何新事物剛推出時的情況一樣,不免會受到一些阻力或至少一絲猶豫。ECAI在接下來的會議裡提到一點:空間或地理數據只是人文領域需求中的一部分,我們也需要為這些發生在經緯線上的思想和實踐發展標記時間,因為它們是一段涉及時間向度的歷史進程。有幾年的時間,我們轉向使用由澳洲悉尼大學開發的TimeMap軟體。這個軟體是Roland Fletcher教授和他底下的兩名研究員Ian Johnson和Damian Evans的共同發想。TimeMap很前衛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創建動態地圖,來顯示某些元素或特徵在地表上的傳播與分佈。這組悉尼團隊非常顯赫的一項創舉是,製作了一個表現蒙古帝國向外擴張的動態地圖,從每年征戰擴大的版圖到最鼎盛遼闊的疆土,然後趨勢逆轉退回到內亞的草原地帶。能夠將數千個隨著時間推進的數據演化透過視覺畫面來呈現,是一大步的躍進。今天的我們倚賴Google Earth等軟體,並將紙本的靜態地圖丟棄在車子前座置物箱裡,這是因為電子地圖可以提供即時的資訊,帶領我們前往目的地。當我開始掀起這類議題的討論後,我受邀去為華盛頓特區國家人文基金會的工作同仁演講。他們從來沒有為使用GIS軟體的學者提供過任何研究資金,雖然大多對於人文領域運用時空索引作為展現手法一事感到不可思議,但卻對此抱持開放態度。我很喜悅的想要告訴大家,至今已有多個獎項頒贈給在研究中使用GIS軟體的學者,地圖繪測技術(Mapping)作為一種研究途徑,目前在多個領域中也已受到認可,而在這個具有巨大開發及應用潛能的地理空間研究沃土上,ECAI只是其中的一小步。
ECAI的其中一個會議在印度南部舉行,就在那次誕生了「海上佛教地圖」的構想。在泰米爾納德邦的會議,發言人當中的Heemanshu Ray教授,是海上貿易史和海上佛教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她在會議中的發表,以及會後我們倆的討論,對「海上佛教地圖」概念的產生至關重要。另一位發表人S. Dayalan博士,是印度考古調查局(ASI)的高級考古學家,他對南印度考古遺址的知識極為廣闊,並且樂於分享資源。在他的邀請之下,我去了欽奈,在欽奈ASI的圖書館呆了好幾天。那裡館藏了南印度考古遺址的實地考察紀錄。我沈浸於閱覽那些田野筆記,但卻也驚訝地發現自己對南印度佛教的認識甚淺。在我的學生時期,經常看到的阿育王政治版圖,其疆土幾乎覆蓋了整個次大陸,唯獨泰米爾納德邦這一塊。當時所獲得的解釋是,泰米爾納德邦在歷史上是達羅毗荼文化的中心,以濕婆教為主要教派,因此甚少有與佛教相關的習俗和實踐。然而,我讀了那些田野筆記之後,發現泰米爾納德邦到處都有佛教場所,甚至還有大型的佛教大學遺址。這與我早期所學到的知識有落差,因此我必須調整對南印度佛教史蹟的原有看法。當我翻閱並留意這些考古挖掘的地點,我的第一直覺是,這些佛教遺址似乎都坐落在沿海一帶。這樣的想法一直繚繞於心,我不斷地思維其含義和印證它的方式。最後,在Dayalan博士的協助下,我們派出由年輕一輩組成的考古團隊,讓他們帶著相機、電腦和GIS軟體進入考古現場。他們重新訪察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的多處遺址,並運用經度和緯度精確地標示出遺址的位置。當蒐集來的數據經分析顯示於地圖上,我那最初想法即獲證實。佛教遺址確實聚集在沿海地區,尤其是海港。在通往海港腹地的河岸邊,也有一些遺址,但相較於鄰近海港的區域,它們的數量較少,且很多只出現在河堤的其中一岸,而不是兩岸都有。我希望有一天能對堤岸進行更多的研究,進一步探討堤岸如何標誌出文化邊界,而河岸兩堤是否擁有各自的文化特色?第三類發現佛教遺址的地點是位於離開港口及河岸的陸路,這些建在陸路上的遺址數量,跟鄰近水源的區域相比,就顯得零星無幾了,而我們可以假設,這些所謂鄰近水源的區域也就是活躍和具有興盛貿易的區域。
證實了佛教遺址主要位於沿海一帶以後,我們便決定繪製「海上佛教地圖」。這時,我接觸到數位開發的另一個走向。也就是在香港城市大學當兼任教授的那個時期,我結識了當時是香港城市大學新媒體藝術中心主任的邵志飛教授,及他的同事莎拉‧肯德丁教授。在開發新式的資料蒐集法和展覽設置,以及採用3D虛擬實境呈現文化資料等方面,他們倆人是世界的領航。我在校園及附近的研究中心看過他們的裝置。其中用來展示敦煌淨土洞窟畫面的沉浸式環境,超乎了我的認知和想像。站在環形式的劇場及被眼前的圖景所包覆,就像身歷其境一樣,這種視覺體驗實在讓人感到震撼。我和肯德丁教授一同討論,這樣的技術能夠如何運用在「海上佛教地圖」的製作,而我們一致的目標是,要將這些資料開放並推廣予普羅大眾和學術界人士。正如敦煌石窟的那個展覽吸引了逾千人前往參觀,我們希望採用同樣的手法於「海上佛教地圖」,讓這個地圖也涵蓋地理和時間向度。肯德丁教授後來到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任職,就在這段時期,我們寫了一份企劃案提交給澳洲研究委員會(ARC),並申請資金讓我們的團隊到印度西岸、斯里蘭卡、東南亞如緬甸、泰國、柬埔寨及爪哇等鄰近島嶼,還有位於中國大陸的東亞貿易港口各地拍攝影像。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而邵教授也加入這個行列。其中最大的障礙,即是獲取相關單位的允可進入這些被列為文化遺產的建築進行錄攝。經過兩年多的談判和妥協,我們才獲得政府的批准。我們的提案僅是為這些拍攝的圖和影像申請使用權,而所有圖和影像的原檔將歸該國家所有。除此之外,我們也向博物館方申請,透過光度立體技術為他們館藏的文物建構虛擬3D模型。在這過程中,肯德丁教授則協助培訓當地的博物館員,作為一種答謝。
終於,我們能將拍攝團隊帶到遺址現場,並使用前衛的科技對文物的各個細節進行全方位的拍攝。在過去的兩年裡,肯德丁教授帶領團隊花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來完成圖像和影像的拍攝。執行這項工作的日程安排,對肯德丁教授和拍攝團隊而言,是一項艱困的磨練。為了能夠捕捉充足的光線,拍攝的最佳時間是在清晨或黃昏時段。也就是說,團隊必須早上四點鐘起床,要趕在第一道曙光之前將一切準備就緒,然後等到即將日落前再回到拍攝地點。有時候,當他們完成了一整天的拍攝,便又夜裡開車趕往下一個地點。肯德丁教授投入在這項拍攝工作中的能耐和永不退懈的堅毅,我永懷感激。我和太太參與過在斯里蘭卡的拍攝,不過只有很短一段時間。雖然時間很短,但我回國後,卻需要吃藥療養一段時間。然而,在所有攝影工作人員、當地相關單位、圖像和影像後製團隊的攜手努力下,肯德丁教授一共從印度、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爪哇和中國等數百個遺址和文物中收集了逾千張的圖像。若沒有她的辛勤付出,這個展覽則不可能成形。
當圖像完成後製和數位化以後,我們便思考,這些成品可以在哪裡展示。我們希望找一個對大眾開放和方便參觀的空間地點。每一項裝置的建構費用都非常的昂貴,也涉及多台投影機、電腦、圖樣設計、文案和文本敘述。我們認為,台灣的一間新博物館-佛陀紀念館,是其中很適合的地點。佛陀紀念館佔地一百英畝,現在已是台灣主要旅遊勝地之一,每年參觀人數可與世界上的多數博物館媲美,甚至更多。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在這場展覽的籌畫中扮演關鍵角色,他的願景和樂意嘗試各種新式展覽,包括這樣的數位虛擬展,這啟發了我們所有人。他協助我們聯繫星雲大師,而大師也同意佛館提供空間、資金和人員配置,讓我們規劃一個長達數年的展覽。在館方和國際策展團隊之間的討論和各項翻譯上,妙光法師則是重要的協調窗口。
在預計於佛陀紀念館舉行世界首展計畫的最後階段,卻面臨疫情帶來的挑戰,博物館關館、飛航限制等改變了整個環境。原定於2020年秋季的展覽開幕不得不取消,並推延至2021年5月。邵教授是這個展覽從構想到建製的靈魂人物,由於這段時間不能夠搭飛機親臨現場,所以他經常是從遠端監督整個策展工程。如今,我們終於迎來即將開展的一刻,必須感謝邵教授和如常法師,在最艱難的時刻依然義無反顧地堅持下去。沒有他們堅毅的信念,就不可能圓滿策展。
如您所見,在這所有的過程中,我經常只是個觀察者角色。我很難想像,有誰會不被這些奉獻所感動──默默地犧牲、漫長的工作時間、無數次的會議、反覆的討論與協調。在十幾年前我參加在泰米爾納德邦舉行的那場會議時,我根本無從預測接下來的發展會是如何。我感謝所有為這個展覽努力付出的朋友,和那些即將前來觀展的人。這是一個成真的美夢。

